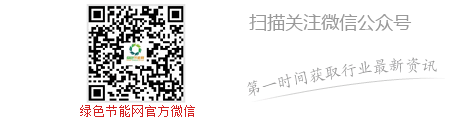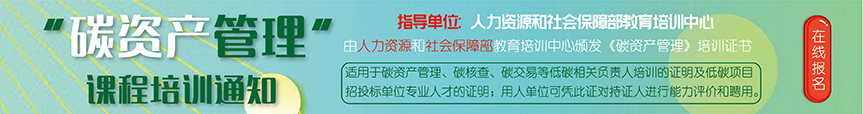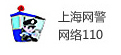2012年08月07日09:03 來源:大洋網-廣州日報 作者:李華 張晨子

水城香港如何治住“龍王”?
曾飽受“水浸街”之苦 香港用“三招鮮”治水23年 成效顯著
做“地下工作”不做“面子工程” 如今可抵御200年一遇洪水
7月23日臺風“韋森特”襲港,香港天文臺自1999年后首次掛上最高警告級別的10號風球應對。幸運的是,香港無人死亡。
在“韋森特”的淫威下,上環(曾經的“水浸街”重災區)并未淪陷為汪洋大海,彌敦道(香港最著名的街道之一)繼續著它的繁華人們曾經戲謔彌敦道為“彌敦河”。香港,一如既往的平靜。
歸根結底,如果沒有1997年后大興土木興建“防洪三招”,香港很難安穩度過這場風暴。“香港市區看海景”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上環永樂街歷史悠久,近街店鋪是出了名的海味街。街道東西走向,全長950米,海拔只有2.64米,是那一帶的最低點,長期以來飽受水患侵擾,每逢暴雨便水流成河,“的士變劃艇”。
不僅如此,永樂街臨近港澳碼頭,潮水倒灌也是家常便飯,除了水淹,長期以來還經受倒灌的折磨。
為消除水患,永樂街修建了“蓄洪池”和“雨水截流隧道”,上環洪水泵房也于2009年3月投入運作,抵御50年一遇的暴雨已不成問題。
香港渠務署高級工程師曾國良對于上環“水浸街”的歷史了如指掌,在上環洪水泵房的海濱長廊上,他邊走邊向記者介紹上環的新貌:圓形廣場、寵物公園、太極園……

香港上環地區的雨水泵房。
可抵御“200年一遇”
屬亞熱帶氣候的香港年平均降雨約2400毫米,在太平洋鄰近地區城市中居于首位,是北京(年降水量在500~600毫米)的4倍。曾國良直言,強降雨量是香港水患成災最重要的原因。
以上是先天性因素,曾國良進而介紹,在后天的高密集度城市發展過程中,香港面積廣大的天然土地被鋪成混凝土路面,從前可被天然土地儲藏的雨水如今成了地面徑流,令淹水問題惡化。
舊城區的渠道建成已幾十年,設施破舊,排水能力不足。降水和排水設施一強一弱,對比強烈,水患的嚴重程度日益突出。
香港每個區域洪水泛濫的原因又各有不同:新界是低洼地,加之渠道淤塞,雨勢一大就雨水泛濫。荃灣、回沖和西九龍,渠道老化,排水系統不足,城市建設導致地表滲水能力不高。上環地區過去也存在地勢低洼和潮汐問題,時常水流成河。
曾國良指著一張圖紙向記者解釋:1990年前,香港新界10余條河道周邊的洪泛平原、東西九龍、港島北幾乎都是易被淹水的地區。香港大面積處于水患包圍之中,少有地區能幸免,即便到了1995年,淹水“黑點”仍多達90個。
1989年9月,香港渠務署成立,肩負起防洪的重任。渠務署進行了一系列的防洪策略研究,包括:公共雨水排放系統的防洪標準、長期的改善措施、預防性維修、應急措施等。
目前,香港已建有三條雨水截流隧道,總長約19.8公里,成為排洪的有效屏障;兩個蓄洪池也已基本建成,容量達109000立方米;容量約60000立方米的跑馬地地下蓄洪池正在建設中,預計2018年年初投入使用,屆時將進一步保護香港免受暴雨侵擾。
此外,2400公里的地下雨水渠和340公里的排水渠道星羅密布地分布在香港的各個街道,成為香港排洪的血管。
經過一系列大刀闊斧的建造,香港市區主干排水渠系統已可抵御200年一遇的洪水,市區支排水渠系統和郊區主要河道、排洪渠亦可抵御50年一遇的洪水。
何為“50年一遇”?“50年一遇的洪水,降水量約為140多毫米/小時,我們現在足以抵御。”曾國良對香港的排水渠系統充滿信心。
在治理前,上環永樂街的水浸情況曾非常嚴重。

上中下游“三招鮮”
在與“洪水猛獸”的長期戰斗中,香港人總結出卓有成效的“防洪三招”可供其他城市借鑒:上游截流、中游蓄洪、下游拓渠。
先說“上游截流”:去過香港的人都知道,灣仔、中環等繁華地區多處于山區下游較平坦的區域。因此,渠務署在半山坡修建了雨水截流隧道,大雨時,山上的雨水會在半山坡就被截住,然后引流到較不繁華、人口較少的地區排放入海,從而疏解下游鬧市區的負荷。“這種方法在市區是最有效的。”曾國良如是評價。
目前,渠務署正在修建3項雨水截流隧道工程,總投資約60億港元。
建設蓄洪池,則是中游市區防洪的不二選擇。大雨時,雨水會被引流到蓄洪池暫存,雨停后再用水泵把池里的水抽排到下游,這種方法分解了下游的壓力。
目前香港有3個蓄洪池,最早、同時也是最大的大坑東蓄洪池建成于2004年,造價4億港元,容量為10萬平方米(相當于40個標準游泳池)。
大坑東蓄洪池之上是一個球場,周邊是公園,綠化很好。它建成后基本解除了旺角的水浸威脅,只在2008年的那場“世紀暴雨”中出現過輕微水淹。
上環的永樂街地勢低,每逢大潮,海水便倒灌,若再降大雨,則海水與半山流下的雨水狹路相逢,兩條水龍相持不下后向街區四溢開來,上環街區便淪為一片汪洋。
為此,渠務署修建了水閘以阻海水倒灌,并在上環中港道建了一個地下蓄洪池和泵房,4臺大型水泵(外加2臺備用水泵)馬力十足,抽水量可達1立方米/秒。如果6臺水泵同時抽一個標準游泳池,7分鐘就可把它抽干。就這樣,永樂街的浸水問題迎刃而解。
跑馬場是灣仔區最低點,同樣容易成為“水浸街”的重災區,2008年那場暴雨中,跑馬場成了個“大水池”,方圓30公頃被淹。
正在修建的跑馬場蓄洪池將有諸多創新之處,渠務署準備用上可自動調校的水閘,并在4個較重要的渠道安裝水位感應器。通過“三維計算流體力學模型”計算出自動調校水閘的最佳位置,以達到最佳的蓄洪效果。
曾國良說,如果不使用新技術,蓄洪池的容量要增大三成才能達到相同效果。因為這項富有創新性的設計,今年7月,香港渠務署在新加坡摘得“2011年國際水協會創新大獎”。
“下游拓渠”是防洪的第三重保險。如果某地區防洪能力不夠強,渠務署通常挖路,更換大號或斜度比較大的渠道,以增加排洪量。通常情況下,挖路會影響公眾的正常出行,渠務署采用“無坑挖掘技術”,對公眾幾乎無影響。
淹水黑點降至15個
“防洪三招”固然有效,但并非一勞永逸,排水系統的日常維護工作并不輕松。渠務署對2400公里地下雨水渠、340公里排水渠和27個鄉村的防洪抽水計劃都會進行定期巡查,排除隱患。
在無人可能進入的現有排水渠內,已大量使用閉路電視進行監控。未雨綢繆,在嚴重問題產生之前,就會及時修理。
此外,渠務署設24小時值班熱線,負責處理市民關于水浸等問題的投訴。
天文臺發出暴雨警告時,政府會立即組織渠務署、民政署、消防處、警察部門等共同組成緊急控制中心,負責協調因大雨造成的水浸、路面交通、人員疏散等問題,渠務署會向部分水浸“黑點”地區的住戶發送預警短信。
防洪同樣離不開居民的支持,為此,渠務署時常走進社區,開展宣教,通俗易懂地傳遞“洪水如猛獸”的意識,讓居民在潛移默化中養成“勿走近河道”的規則。
“市民一小步,防洪一大步。”曾國良認為防洪宣教非常重要。
渠務署成立以來,在防洪方面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效,曾國良喜歡用數據說話,因為“數據不會說謊”。他說,1995年未建大型工程以前,全香港淹水黑點有90個。工程陸續完成后,水浸黑點減少到15個。
他滿懷憧憬地展望未來:“還有大型工程在建造、籌劃中,我們希望未來5~10年可以把余下的15個黑點處理掉。”
有時他也有些沮喪和無奈。渠務署的工作主要是防洪,做的是“地下工作”而不是“面子工程”,市民不能直接感受到,因此,渠務署的工作很難得到市民充分的肯定。
“香港模式”不可照搬
如上所述,渠務署把所有的集水區都分成上游、中游、下游三部分,上游的水由雨水截流隧道排放;中游的問題由蓄洪池解決;下游通過渠道排水。據估算,如果沒有前兩道防線,所有的雨水都會集中到下游,香港渠務署需要處理面積約400公頃的雨水;而有了前兩道防線,需處理的雨水面積被減少至80公頃,常規工程就可解決。
曾國良向記者開玩笑地說:“如果沒有前兩個步驟,可能下游的每一條道路都需要我們挖開來鋪渠道。”
“防洪三招”招招有效,曾國良以香港島為例向記者算了一筆賬:雨水截流隧道半路攔截雨水,使雨水未到市區就已被卸去四成,蓄洪池和排水渠又各卸三成雨水,港島的內澇問題基本解決。
不過,曾國良強調這三招不可原樣照搬,否則可能“水土不服”。比如,香港市區有后山,前平后高,憑借地勢特點才能在山坡建雨水截流隧道。內地沒有山坡的地區如果也用這種方法,肯定不如香港有效,可能用蓄洪池更科學。
香港的蓄洪池多半建在公地,因為購買私人用地時間長、成本高,維修也有諸多不便。選址時,優先考慮地勢低的公地,這樣可有效收集雨水。蓄洪池的大小取決于集水區的范圍,水量是最大的考量標準,九龍和大坑東蓄洪池收集的范圍有幾百公頃,容量也相應較大。
香港靠海,排水有天然地勢;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內地沒有海的地區無可作為可以把水排到附近的河道。
曾國良認為,防洪要“排蓄為主,先蓄后排”,首先得找一個合適的地方蓄洪,如果找不到現成的,就進行地區性改造,建造一個比較大的排洪渠道,改善排洪能力。洪水來襲時,日本、臺灣地區利用天然湖泊、低位球場蓄洪,他認為這值得借鑒,因為建造地下蓄洪池成本很高。
他一再強調“因地制宜”:“這三招對香港非常有效,應用到廣州、北京時要考慮當地的特性,不同地區要有不同的策略。”
在多年的工作中,曾國良總結出一套“治水”心得:防洪要先做規劃,詳細研究每個地區的水患原因,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根據各個地方的重要性制定不同的防洪標準,市區是城市的心臟,重要性最高,防洪標準也應該最嚴;鄉村人口較少,重要性相對次之。通常的做法是,在小村外圍筑防洪堤,防止洪水涌入村內。


保存到相冊
|
曾飽受“水浸街”之苦 香港用“三招鮮”治水23年 成效顯著
做“地下工作”不做“面子工程” 如今可抵御200年一遇洪水
7月23日臺風“韋森特”襲港,香港天文臺自1999年后首次掛上最高警告級別的10號風球應對。幸運的是,香港無人死亡。
在“韋森特”的淫威下,上環(曾經的“水浸街”重災區)并未淪陷為汪洋大海,彌敦道(香港最著名的街道之一)繼續著它的繁華人們曾經戲謔彌敦道為“彌敦河”。香港,一如既往的平靜。
歸根結底,如果沒有1997年后大興土木興建“防洪三招”,香港很難安穩度過這場風暴。“香港市區看海景”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上環永樂街歷史悠久,近街店鋪是出了名的海味街。街道東西走向,全長950米,海拔只有2.64米,是那一帶的最低點,長期以來飽受水患侵擾,每逢暴雨便水流成河,“的士變劃艇”。
不僅如此,永樂街臨近港澳碼頭,潮水倒灌也是家常便飯,除了水淹,長期以來還經受倒灌的折磨。
為消除水患,永樂街修建了“蓄洪池”和“雨水截流隧道”,上環洪水泵房也于2009年3月投入運作,抵御50年一遇的暴雨已不成問題。
香港渠務署高級工程師曾國良對于上環“水浸街”的歷史了如指掌,在上環洪水泵房的海濱長廊上,他邊走邊向記者介紹上環的新貌:圓形廣場、寵物公園、太極園……


保存到相冊
|
可抵御“200年一遇”
屬亞熱帶氣候的香港年平均降雨約2400毫米,在太平洋鄰近地區城市中居于首位,是北京(年降水量在500~600毫米)的4倍。曾國良直言,強降雨量是香港水患成災最重要的原因。
以上是先天性因素,曾國良進而介紹,在后天的高密集度城市發展過程中,香港面積廣大的天然土地被鋪成混凝土路面,從前可被天然土地儲藏的雨水如今成了地面徑流,令淹水問題惡化。
舊城區的渠道建成已幾十年,設施破舊,排水能力不足。降水和排水設施一強一弱,對比強烈,水患的嚴重程度日益突出。
香港每個區域洪水泛濫的原因又各有不同:新界是低洼地,加之渠道淤塞,雨勢一大就雨水泛濫。荃灣、回沖和西九龍,渠道老化,排水系統不足,城市建設導致地表滲水能力不高。上環地區過去也存在地勢低洼和潮汐問題,時常水流成河。
曾國良指著一張圖紙向記者解釋:1990年前,香港新界10余條河道周邊的洪泛平原、東西九龍、港島北幾乎都是易被淹水的地區。香港大面積處于水患包圍之中,少有地區能幸免,即便到了1995年,淹水“黑點”仍多達90個。
1989年9月,香港渠務署成立,肩負起防洪的重任。渠務署進行了一系列的防洪策略研究,包括:公共雨水排放系統的防洪標準、長期的改善措施、預防性維修、應急措施等。
目前,香港已建有三條雨水截流隧道,總長約19.8公里,成為排洪的有效屏障;兩個蓄洪池也已基本建成,容量達109000立方米;容量約60000立方米的跑馬地地下蓄洪池正在建設中,預計2018年年初投入使用,屆時將進一步保護香港免受暴雨侵擾。
此外,2400公里的地下雨水渠和340公里的排水渠道星羅密布地分布在香港的各個街道,成為香港排洪的血管。
經過一系列大刀闊斧的建造,香港市區主干排水渠系統已可抵御200年一遇的洪水,市區支排水渠系統和郊區主要河道、排洪渠亦可抵御50年一遇的洪水。
何為“50年一遇”?“50年一遇的洪水,降水量約為140多毫米/小時,我們現在足以抵御。”曾國良對香港的排水渠系統充滿信心。

保存到相冊
|

上中下游“三招鮮”
在與“洪水猛獸”的長期戰斗中,香港人總結出卓有成效的“防洪三招”可供其他城市借鑒:上游截流、中游蓄洪、下游拓渠。
先說“上游截流”:去過香港的人都知道,灣仔、中環等繁華地區多處于山區下游較平坦的區域。因此,渠務署在半山坡修建了雨水截流隧道,大雨時,山上的雨水會在半山坡就被截住,然后引流到較不繁華、人口較少的地區排放入海,從而疏解下游鬧市區的負荷。“這種方法在市區是最有效的。”曾國良如是評價。
目前,渠務署正在修建3項雨水截流隧道工程,總投資約60億港元。
建設蓄洪池,則是中游市區防洪的不二選擇。大雨時,雨水會被引流到蓄洪池暫存,雨停后再用水泵把池里的水抽排到下游,這種方法分解了下游的壓力。
目前香港有3個蓄洪池,最早、同時也是最大的大坑東蓄洪池建成于2004年,造價4億港元,容量為10萬平方米(相當于40個標準游泳池)。
大坑東蓄洪池之上是一個球場,周邊是公園,綠化很好。它建成后基本解除了旺角的水浸威脅,只在2008年的那場“世紀暴雨”中出現過輕微水淹。
上環的永樂街地勢低,每逢大潮,海水便倒灌,若再降大雨,則海水與半山流下的雨水狹路相逢,兩條水龍相持不下后向街區四溢開來,上環街區便淪為一片汪洋。
為此,渠務署修建了水閘以阻海水倒灌,并在上環中港道建了一個地下蓄洪池和泵房,4臺大型水泵(外加2臺備用水泵)馬力十足,抽水量可達1立方米/秒。如果6臺水泵同時抽一個標準游泳池,7分鐘就可把它抽干。就這樣,永樂街的浸水問題迎刃而解。
跑馬場是灣仔區最低點,同樣容易成為“水浸街”的重災區,2008年那場暴雨中,跑馬場成了個“大水池”,方圓30公頃被淹。
正在修建的跑馬場蓄洪池將有諸多創新之處,渠務署準備用上可自動調校的水閘,并在4個較重要的渠道安裝水位感應器。通過“三維計算流體力學模型”計算出自動調校水閘的最佳位置,以達到最佳的蓄洪效果。
曾國良說,如果不使用新技術,蓄洪池的容量要增大三成才能達到相同效果。因為這項富有創新性的設計,今年7月,香港渠務署在新加坡摘得“2011年國際水協會創新大獎”。
“下游拓渠”是防洪的第三重保險。如果某地區防洪能力不夠強,渠務署通常挖路,更換大號或斜度比較大的渠道,以增加排洪量。通常情況下,挖路會影響公眾的正常出行,渠務署采用“無坑挖掘技術”,對公眾幾乎無影響。
淹水黑點降至15個
“防洪三招”固然有效,但并非一勞永逸,排水系統的日常維護工作并不輕松。渠務署對2400公里地下雨水渠、340公里排水渠和27個鄉村的防洪抽水計劃都會進行定期巡查,排除隱患。
在無人可能進入的現有排水渠內,已大量使用閉路電視進行監控。未雨綢繆,在嚴重問題產生之前,就會及時修理。
此外,渠務署設24小時值班熱線,負責處理市民關于水浸等問題的投訴。
天文臺發出暴雨警告時,政府會立即組織渠務署、民政署、消防處、警察部門等共同組成緊急控制中心,負責協調因大雨造成的水浸、路面交通、人員疏散等問題,渠務署會向部分水浸“黑點”地區的住戶發送預警短信。
防洪同樣離不開居民的支持,為此,渠務署時常走進社區,開展宣教,通俗易懂地傳遞“洪水如猛獸”的意識,讓居民在潛移默化中養成“勿走近河道”的規則。
“市民一小步,防洪一大步。”曾國良認為防洪宣教非常重要。
渠務署成立以來,在防洪方面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效,曾國良喜歡用數據說話,因為“數據不會說謊”。他說,1995年未建大型工程以前,全香港淹水黑點有90個。工程陸續完成后,水浸黑點減少到15個。
他滿懷憧憬地展望未來:“還有大型工程在建造、籌劃中,我們希望未來5~10年可以把余下的15個黑點處理掉。”
有時他也有些沮喪和無奈。渠務署的工作主要是防洪,做的是“地下工作”而不是“面子工程”,市民不能直接感受到,因此,渠務署的工作很難得到市民充分的肯定。
“香港模式”不可照搬
如上所述,渠務署把所有的集水區都分成上游、中游、下游三部分,上游的水由雨水截流隧道排放;中游的問題由蓄洪池解決;下游通過渠道排水。據估算,如果沒有前兩道防線,所有的雨水都會集中到下游,香港渠務署需要處理面積約400公頃的雨水;而有了前兩道防線,需處理的雨水面積被減少至80公頃,常規工程就可解決。
曾國良向記者開玩笑地說:“如果沒有前兩個步驟,可能下游的每一條道路都需要我們挖開來鋪渠道。”
“防洪三招”招招有效,曾國良以香港島為例向記者算了一筆賬:雨水截流隧道半路攔截雨水,使雨水未到市區就已被卸去四成,蓄洪池和排水渠又各卸三成雨水,港島的內澇問題基本解決。
不過,曾國良強調這三招不可原樣照搬,否則可能“水土不服”。比如,香港市區有后山,前平后高,憑借地勢特點才能在山坡建雨水截流隧道。內地沒有山坡的地區如果也用這種方法,肯定不如香港有效,可能用蓄洪池更科學。
香港的蓄洪池多半建在公地,因為購買私人用地時間長、成本高,維修也有諸多不便。選址時,優先考慮地勢低的公地,這樣可有效收集雨水。蓄洪池的大小取決于集水區的范圍,水量是最大的考量標準,九龍和大坑東蓄洪池收集的范圍有幾百公頃,容量也相應較大。
香港靠海,排水有天然地勢;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內地沒有海的地區無可作為可以把水排到附近的河道。
曾國良認為,防洪要“排蓄為主,先蓄后排”,首先得找一個合適的地方蓄洪,如果找不到現成的,就進行地區性改造,建造一個比較大的排洪渠道,改善排洪能力。洪水來襲時,日本、臺灣地區利用天然湖泊、低位球場蓄洪,他認為這值得借鑒,因為建造地下蓄洪池成本很高。
他一再強調“因地制宜”:“這三招對香港非常有效,應用到廣州、北京時要考慮當地的特性,不同地區要有不同的策略。”
在多年的工作中,曾國良總結出一套“治水”心得:防洪要先做規劃,詳細研究每個地區的水患原因,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根據各個地方的重要性制定不同的防洪標準,市區是城市的心臟,重要性最高,防洪標準也應該最嚴;鄉村人口較少,重要性相對次之。通常的做法是,在小村外圍筑防洪堤,防止洪水涌入村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