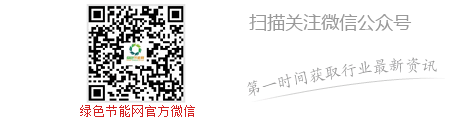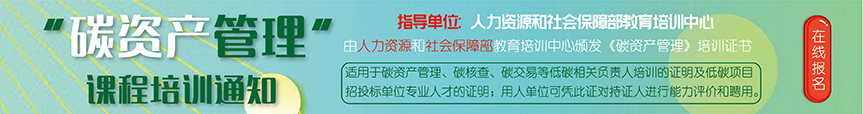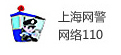增塑劑是大陸的常用說法,但在臺灣塑化劑風波的裹挾中,現在都稱為塑化劑。塑化劑是所有塑料助劑中用量最大的。其中性價比最優的鄰苯二甲酸酯 類使用最為廣泛,全球每年的使用量在800 萬噸以上,其中以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為主體,占了75%的份額。其中鄰苯二甲酸二異辛酯(DEHP)生產最多,其次就是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前者DEHP,在臺灣塑化劑風波中一枝獨秀,DBP只是敲了一下邊鼓,這次終于在酒鬼酒事件中成為主角。
不過二者的出場方式有所不同,DEHP是蓄意添加,屬于主觀故意;DBP目前被認為屬于定向遷移所致。鄰苯二甲酸酯類在塑料中老實呆著的時候,和人類是和平共處的,發揮的都是好作用,它可以增加塑料的柔韌度。但鄰苯類塑化劑容易逃逸到環境中,這時發揮的都是環境內分泌干擾物的壞作用。塑化劑可通過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及皮膚接觸等途徑進入人體,具有生殖毒性和發育毒性,這種危害也是隱蔽而漫長的。“鄰二甲苯酸酯綜合征”就是專指被鄰苯二甲酸酯類化合物,特別是DEHP、DBP、BBP染毒之后,雄性嚙齒類動物表現出生殖系統畸形和乳頭殘留等癥狀。

以中國長江三角洲地區為例,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鄰苯二甲酸二丁酯在環境和人體生物樣品中廣泛存在。食物是人體攝入塑化劑的主要攝入途徑,占總攝入量的90%左右,其次為飲用水,占8%左右。DEHP和DBP被美國環保局列為優先控制污染物,歐盟也將DBP作為高風險評估的管控物質,中國也已經將其列入環境優先污染物黑名單。

規范的白酒釀造生產過程中是不可能產生塑化劑的。陶盆瓦罐草墊麻繩的作坊時代,白酒里面也定是沒有塑化劑。自上個世紀70年代塑料制品遍地開花,40年來塑化劑就悄悄地進入酒中了,這屬于特定遷移,源于塑料接酒桶、塑料輸酒管、酒泵進出乳膠管、封酒缸塑料布、成品酒塑料內蓋、成品酒塑料袋包裝、成品酒塑料瓶包裝、成品酒塑料桶包裝等等不一而足,每一個和塑料親密接觸的環節都是隱患,小到最后瓶蓋的軟膠墊都可能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高檔酒因為酒精度數高,塑化劑溶解度相應高,因為貯存年份長,塑化劑溶解量相應大。
一年半前,酒協在臺灣塑化劑風波后,就明令禁止酒企業用塑料制品,但是看來未能做到令行禁止。事發前一個月,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國家質檢總局曾聯合對市場上流通的主要白酒品牌進行暗訪抽查,確實發現部分白酒產品中含有塑化劑成分,但并未超出衛生部相關規定的限值。
當然,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不排除釀造是個概念,實則是由劣質香精勾兌的酒,這就有可能香精本身就是用鄰苯類塑化劑來做香料溶劑及定香的,那么塑化劑就會混入其間。至于加塑化劑掛壁之說,姑且可以認為是一種主觀臆測,因為掛壁濃稠和酒體清澈透亮不可兼得,陳年老窖的濃釅不是塑化劑可以仿制的,就算塑化劑超標動輒上百倍的飲料也未見得掛壁了,只是均勻懸浮而已,所以從檢測出來的超標數量級來看,至少此次送檢的樣品人為添加的可能性較小。

酒鬼酒中超標的DBP,盡管尚未列為致癌物,但后者的ADI值小于前者,生殖毒性更強。需要強調的是,鄰苯類塑化劑的主要危害不是致癌毒性,而是生殖毒性。值得慶幸的是,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根據國際通用風險評估方法和歐洲食品安全局推薦的人體可以耐受攝入量,取第三方檢測機構的酒鬼酒中DBP含量為1.08mg/kg 計算,按照我國人均預期壽命,每天飲用1斤,其中的DBP不會對健康造成損害。絕大部分塑化劑在24 至48 小時內會隨尿液或糞便排出體外。只要停止攝入含有塑化劑的食品,體內塑化劑 濃度便會快速下降。
從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鄰苯類塑化劑取代樟腦成為塑料業的新寵,發達國家瘋狂地使用,但是現在已經懸崖勒馬,限制生產和添加了,而我們卻成為了鄰苯類塑化劑生產和使用大國。美國現在是環境友好無毒塑化劑最大的生產商,中國改弦易轍調整塑化劑生產方略,大力發展檸檬酸酯類、環丙酸酯類等無毒塑化劑就迫在眉睫了,作為檸檬酸第二大生產國,有做大做強檸檬酸酯類塑化劑的底氣。終究,不用鄰苯類塑化劑,才是硬道理,否則覆巢之下難有完卵,這次是白酒中槍,下次可能是和塑料親密接觸的其他,將會層出不窮。
結語:此次酒鬼酒中查出過量塑化劑,但生活中還有可能出現更多此類情況。日常生活中,在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圍內,減少塑化劑的攝入是關鍵,比如油瓶不用塑料的,泡方便面改用瓷碗,泡腳盆不用塑料袋蒙著,吃香辣蟹不用薄膜手套等等,這些比少喝酒關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