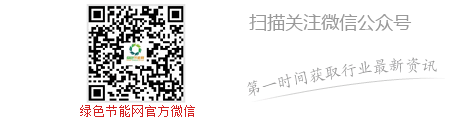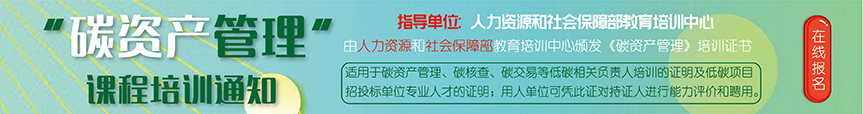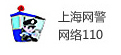編者按:四大淡水湖邊的創傷和記憶
遠離三峽,我們來到四大淡水湖,查閱真實的湖泊病歷。
此刻,驟然風雨,旱澇已急轉,誰還能摸準湖泊的脾氣?高峽大壩,爭議仍紛然,誰還篤信人力定勝天?
四大淡水湖的今昔,見證著這些疑問和感慨。我們幼年時,讀著教科書里的四大湖,才知道幅員遼闊,物產豐饒;我們成長中,沉醉于發展才是硬道理,哪怕“山無棱,江水為竭”。
現在,我們困擾了,被迫彌補了,方驚覺豈能畢其功于一役。
我們努力只觀察,不判斷,因為每個湖泊都是生命體,癥結病灶不能只靠簡單的望聞問切。
我們不討巧,用拙筆,就像封面的這兩只碗,今昔對比,觸目驚心。
我們相信:有姿態,就有立場。我們試圖還原鄱陽湖的一段自救夢想,描摹洞庭湖的某些生態片段,追溯太湖的污染背影,甚至只是聽聽洪澤湖漁民的家長里短。
記下湖泊病歷,關注湖泊命運,更是關注我們自己。

從瀕危的江豚到“四大家魚”,從水草到底棲動物,還有多年為患的東方田鼠,洞庭湖生態系統岌岌可危。而這,也不單單是洞庭湖的危機。
“春自生,冬自槁,須知湖亦如人老。”清代詩人袁枚曾如是描摹洞庭湖四季榮枯之道。然而2011年春末夏初,本應“浩浩湯湯,橫無際涯”的洞庭湖提前“老”了。
6月2日上午,蔣勇站在洞庭湖的大堤上,放眼望去,洲灘處處,牛羊低首,芳草萋萋,沙鷗翔集。“似曾相識,時空倒錯。”這名世界自然基金會(簡稱WWF)長沙項目辦官員感慨道。他去年才卸任東洞庭湖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副局長。原本,這一派郁郁青青應是冬日風景,而今卻吊詭地成了夏季奇觀。
蔥蘢幻象之下,八百里洞庭的生態裂痕已然浮現。隱憂早已有之,因這次不期而至的旱殤而重現、放大。

東洞庭湖,一名漁民在曬魚干。據岳陽市魚政站統計,由于魚類資源的減少,06年漁民的捕撈量明顯不如往年。 (新京報 楊振華/CFP/圖)
江豚告急
6月4日下午,湖北天鵝洲長江豚類自然保護區的技術負責人龔成躺在醫院里,脾臟已被拆除,右眼的血淤仍未散去。此前十天,與保護區毗鄰的監利縣農民一百余人沖進了保護區,把龔成打成重傷。
如果不是干旱,這樣的悲劇應可避免。大旱之際,監利二十余萬畝農田告急。5月,監利農民先是從保護區所在的長江天鵝洲故道開閘引水,后直接架泵抽水。
水深驟降,負責守護故道內三十余頭江豚的保護區管理人員心如火燒。“江豚從來沒有在這么低的水位里生活過。”保護區管理局主任胡良慧憂心地說,正常情況下水深要達到五米以上,江豚才能自由呼吸,而現在平均水深只有兩米左右。
從5月13日至5月26日,保護區向農業部、湖北省水產局等上級單位連發3道“緊急情況反映”,稱“監利縣強行在保護區內取水抗旱,江豚將面臨滅頂之災”。
一場人與江豚爭水的悲劇由此產生。而這不過是旱殤危及八百里洞庭生態的一個極端案例。事實上,江豚告急的號角在洞庭湖區及至整個長江都早已吹響。
WWF資料顯示,1993年長江至少有2700頭江豚,這個數字到今天已經銳減近一半,其中有150~200頭江豚分布在洞庭湖區。
洞庭湖江豚多年來飽嘗命喪之虞。2004年,岳陽為迎接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的召開,在洞庭湖區投放了約5000噸殺釘螺藥劑,曾釀下一個月內毒死6頭江豚的慘劇。WWF今年初的一項科考顯示,在洞庭湖冬季江豚唯一的棲息區,有眾多的挖沙船、運沙船在頻繁作業,偶爾還有電打魚船。湖水渾濁,比白鰭豚還古老、比大熊貓還稀少的江豚就這樣浮沉于不安的江湖。
大旱又令本已岌岌可危的江豚雪上加霜。湖南師范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楊波教授提供的遙感地圖顯示,5月27日,洞庭湖水面面積僅650平方公里,僅為正常年份同期的七分之一,這也就意味著江豚的生存空間在縮水。5月19日下午,東洞庭湖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在一處水域監測發現,僅2分鐘就監測到51頭次江豚。“這個監測數值說明江豚密度非常大。”管理局高工張鴻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意味著洞庭湖航道變窄,使得江豚棲息區域變小。
而更令蔣勇擔憂的是,每年的4月至6月是洞庭湖的禁漁期,隨著7月1日開漁,大量的漁民將涌進這本就已狹窄的湖面,大旱已令魚類數量銳減,“人與江豚爭食的一幕即將上演”。
難擺尾的江豚不過是整個洞庭湖食物鏈頂端最為敏感的一環。順著江豚的食物鏈逐漸下探,同樣的隱憂亦不鮮見。
魚未上灘
時隔五年,蔣勇仍清晰記得,2006年夏天,洞庭湖君山農場附近的洲灘只被淹沒了七天。水退之后,洲灘裸露的水草上都掛滿了魚卵。每到5月,在密密麻麻的沉水植物間產卵已是洞庭魚兒的習慣。然而今年,沙洲不見水,魚兒未上灘。
“這無疑令本就脆弱的生態系統雪上加霜。”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劉家壽說,魚類產卵需要兩個刺激條件,一靠漲水,二靠洪峰。兩者皆無,洞庭魚兒只得望灘興嘆。
大旱不過是為洞庭魚兒銳減趨勢再添了一枚下墜的砝碼。湖南省漁業環境監測站從1997到2006年連續十年的監測研究發現,洞庭湖魚類捕撈產量下降了近一半,其中“四大家魚”(青魚、草魚、鰱魚、鳙魚)以每年近350噸的數量遞減,“四大家魚”在整個洞庭湖捕魚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由1963年的21%下降到2006年的6.61%,而且捕獲魚類的低齡化、個體小型化趨勢不斷加劇。“四大家魚”已成洞庭湖天然漁業資源中“難得一見”的品種。
湖區各通航水系水工建筑的興建是主要“兇手”,大壩切斷了魚類的洄游通道。據統計,解放后,在洞庭湖區通航河流上共建設了130余座大壩,其中,1998年建成的湘江大垣渡水利工程和2003年截流的三峽大壩影響尤其嚴重。三峽截流后第一年,“四大家魚”在洞庭湖漁獲物中的比重即由10%降到了7.73%。
建國后直至“文革”,在“向湖面要糧”的號召下,洞庭湖區經歷了三次大規模的圍湖造田。1990年代末,造紙業驅動“種楊風”,被列入“中國第一批外來入侵物種”的意大利楊和美國黑楊迅速占領大片濕地,圍困洞庭湖。凡是種種,不僅令濕地生態景觀易色,更令魚類的索餌場和產卵場大幅縮減。
湖區漁民竭澤而漁的沖動亦難辭其咎。
劉明發捕魚為生15年了,他是布設“迷魂陣”的一把好手,以竹竿和紗網織就的陷阱,令大小魚兒有進無出。這種已被當地漁政部門列入黑名單的捕魚招數,迄今仍被洞庭漁民廣為使用。
另一種招數是“打圍”,利用洞庭湖榮枯規律,漲水前在湖灘上筑起高矮不等的堤壩,布下天羅地網,一俟漲水,魚蝦盡入,在劫難逃。雖政府明令禁止,但目前少則幾百畝多則上萬畝的“圍子”仍不鮮見。“只有有關系的‘漁霸’才有實力打圍。”劉明發既羨又恨。
同樣禁而不止的非法捕魚方式還有電捕魚。“洞庭湖上的漁民幾乎沒有不用電捕魚的。”劉明發說,“現在單純靠傳統的撒網下鉤已經很難捕到魚了。”
十年之前,船行湖上,劉明發還不時可見因產卵興奮的魚兒在水面亂跳,但這一幕已成往事。
湖中生態岌岌可危,湖邊濕地亦危機四伏。

(葉首衛/CFP/圖)
濕地危機
6月3日開始,渴極了的洞庭湖終于盼來了降雨。因干涸而皴裂的湖床痊愈了,瘋長的蘆葦和苔草更顯清翠,2625平方公里的洞庭湖濕地顯出詭異的郁郁青青,一反洞庭湖生物鐘,如海市蜃樓。
一個懸在洞庭濕地上的隱憂是:鼠患還會來嗎?2007年,20億只東方田鼠大鬧洞庭,令洞庭人觸目驚心。中科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王勇研究員說,鼠患爆發的首要原因是干旱導致湖灘裸露時間過長進而延長了東方田鼠的繁殖期。此外,“圍湖造田”、“圍湖滅螺”人為改變了湖區生態環境,令東方田鼠的生活地盤擴大。
肇始于1970年代后期的捕蛇狂潮為東方田鼠掃清了天敵。據東洞庭湖自然保護區春風管理站副站長宋濤回憶,在十余年前,洞庭湖的蛇類被成噸販賣到廣東等地。直至今日,洞庭湖區一道名為“口味蛇”的名吃卻已需要廣東等地的蛇類來填空。
今年干旱較之當年更烈,失衡的洞庭生態依舊,將爆發新一輪鼠患的憂慮漸次見諸報端。不過,在多年跟蹤研究洞庭湖東方田鼠的王勇看來,此輪鼠患或許不會形成。根據中科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今年1月至5月的連續監測,今年洞庭湖區東方田鼠的種群數量有所降低。在往年鼠患嚴重的大通湖監測點,東方田鼠的捕獲率較往年同期下降了約30%。
饒是如此,鑒于東方田鼠災害具有爆發性和突發性,5月底呈報給農業部的一份內部簡報上仍這樣寫道:“隨著雨季的到來,湖區水位的上漲,其(東方田鼠)遷移危害農業生產安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鼠患或將不似當年兇猛,但這片中國最大的淡水濕地并不太平。
5月底,中科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的博士生李峰走了一遭洞庭,他驚奇地發現,因為此次干旱,在一些地區,辣蓼等沉水植物已然絕跡,菹草、苦草等亦大幅減少。“這對整個洞庭湖的生物多樣性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這些都是洞庭湖常見的水草,是整個洞庭濕地生態的基石。
洞庭湖濕地被譽為“觀鳥天堂”,然而危機已擺在了眼前。“蚌、螺等大量底棲動物已經死亡,這將會對冬天來此過冬的候鳥產生極大影響。”正在湖區濕地觀鳥的東洞庭湖自然保護區技術科科長姚毅說。而因缺乏足夠的食物和水,正在此棲居的夏季候鳥已開始向濕地外圍轉移。據保護區總工張鴻介紹,洞庭湖濕地遷徙鳥類數量有可能從2012年開始下降,至少需要三至五年的時間才能恢復。
洞庭湖底棲動物的減少也并非自大旱始。僅以螺螄為例,據漁民劉明發稱,以往洞庭湖中無以計數的螺螄現在已經少得可憐。近年來,隨著湖北洪湖、監利等地螃蟹養殖業的迅猛發展,洞庭湖中的螺螄作為螃蟹的優質餌料,被廣為采購運往湖北。三五年前極盛之時,一個漁民一天就可捕撈4000斤螺螄,然而,盛景早已不在。
作為生物鏈里的初級消費者,底棲動物數量銳減乃至絕跡,對整個生態系統的打擊不言而喻。“沒有了底棲動物,洞庭湖還是洞庭湖嗎?”東洞庭湖自然保護區春風管理站副站長宋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