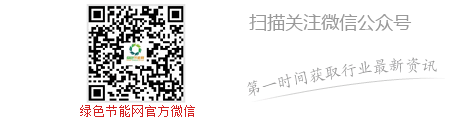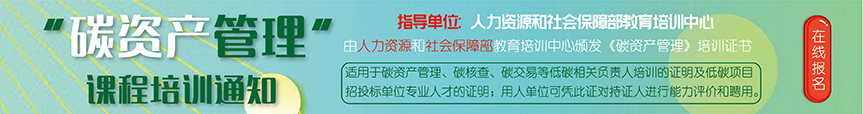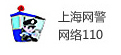黨中央、國務院一直高度重視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工作。“十一五”以來,提出了建設“兩型社會”發展任務,并在節能減排目標約束、責任考核、重點行業企業管理等方面實施了一系列措施行動,取得了明顯的成效,2005年以來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了35%。但從整體上看,我國資源無節制消耗、生態環境退化的趨勢沒有根本轉變,大氣、淡水、土壤、海洋等常規污染日趨嚴重,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快速上升,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嚴重損害人民群眾健康,而且危及公共安全與社會和諧,已經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亟待解決的主要短板問題。
我國資源環境生態矛盾突出,主要源于長期形成的粗放發展模式。2015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達43.0億噸標準煤,煤炭消費總量達39.3億噸,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高達64%。能源利用效率水平整體偏低,單位GDP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是發達國家水平的4-6倍。與發達國家普遍進入油氣時代、部分發達國家開始步入可再生能源時代相比,我國能源發展仍然建立在低質、高碳的基礎上。從國際視野看,2015年,我國人均GDP僅8016美元,不足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水平的1/4;人均能源消費僅3.1噸標準煤,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未來一段時期,我國人口數量還將持續增長,人均GDP水平將不斷上升,能源消費繼續增加的趨勢不會轉變,如果延續目前傳統發展道路,無論從資源保障、生態環境,還是能源安全、經濟代價看都難以支撐。轉變能源發展模式,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迫切內在要求。
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加強資源環境生態特別是能源消耗上限管控,是從源頭上保障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安全、倒逼發展質量和效益提升的關鍵。當前,我國能源供大于求問題突出,能源價格持續低位,生態環境等外部成本尚沒有完全內部化,僅僅依靠市場價格信號,還很難形成推動全社會強化節能減排、保護生態環境的內生動力。強化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管控,并不是限制能源消費增長,也不是“一刀切”,而是在因地制宜、保障各地區能源合理需求增長的前提下,推動能源利用效率和質量效益顯著提升。紅線管控制度不僅僅針對門檻準入,也涉及供應轉變、消費引導,這不僅有利于促進我國資源利用效率和競爭力不斷提升,也有利于保障生態環境產品可持續供給,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
紅線管控制度不是對行政手段的強化,而是通過完善相關法規標準、目標體系、分解落實機制、監管體系、問責制度等,推進生態文明領域的治理體系現代化。實行資源消耗上限管理、建立相關紅線管控制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核心作用是推動節能和大幅提高能效成為滿足需求增長的“第一能源”,推動清潔低碳能源成為能源供應主體,推動減少粗放發展方式帶來的各種浪費,在全社會形成節約適度高效的消費文化和模式。未來一段時期,通過完善紅線管控等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確保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同時,重現天藍、地綠、山青、水秀的生態環境,既對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必將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做出更大貢獻。